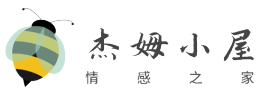我對門的老租客退房之后,住進了一位女..
談學文藝的甘苦
朱光潛(1897~1986),字孟實,安徽桐城人,美學家、教授。著有《給青年的十二封信》、《談美》、《詩論》、《談文學》、《孟實文鈔》等。
親愛的朋友們:
這個題目是尊先生出給我做的。他說常接到諸位的信,怪我近來少替《中學生》寫文章,現在《中學生》預備出“文藝特輯”,希望我說幾句切實的話。諸位的厚意實在叫我萬分慚愧。我從前常給諸位寫信時,自己還是一個青年,說話很自在,因為我知道諸位把我當作一個伙伴看待。眼睛一轉,我現在已經糊糊涂涂地闖進中年了。因為教書,和青年朋友們接觸的機會還是很多,但是我處處感覺到自己已從青年儕輩中落伍出來了。我雖然很想他們仍然把我看作他們中間一個人,但是彼此中間終于是隔著一層什么似的,至少是青年朋友們對于我存有幾分歧視。這是常使我覺得悲哀的一件事。我歇了許久沒有說話,一是沒有工夫去說,二是沒有興會去說,三是沒有勇氣去說。至于我心里卻似一個多話的老年人困在寂寞里面,常渴望有耐煩的年輕人聽他嘮叨地剖白心事。
我擔任的是文學課程。那經院氣十足的文藝理論不但諸位已聽膩了,連我自己也說膩了。平時習慣的謙恭不容許我說我自己,現在和朋友們通信,我不妨破一回例。我以為切己的話才是切實的話,所以我平時最愛看自傳、書信、日記之類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文字。我假定你也是這樣想,所以在這封信里我只說一點切身的經驗。我所說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感想,請恕我蕪雜沒有系統。
我對于做人和做學問,都走過許多錯路。現在回想,也并不十分追悔。每個人的路都要由他自己摸索出來。錯路的教訓有時比任何教訓都更加深切。我有時幻想,如果上帝允許我把這半生的賬一筆勾銷,再從頭走我所理想的路,那是多么一件快事!但是我也相信,人生來是“事后聰明”的,縱使上帝允許我“從頭再做好漢”,我也還得要走錯路。只要肯摸索,到頭總可以找出一條路來。世間只有生來就不肯摸索的人才會墮落在迷坑里,永遠遇不著救星。
一般人常說,文藝是一種避風息涼的地方。在窮愁寂寞的時候,它可以給我們一點安慰。這話固然有些道理,但亦未必盡然。最感動人的文藝大半是苦悶的呼號。作者不但宣泄自己的苦悶,同時也替我們宣泄了苦悶,我們覺得暢快,正由于此。不過同時,偉大的作家們也傳授我們一點嘗受苦悶的敏感。人生世相,在健康的常人看,本來是不過爾爾,朦朧馬虎地過活,是最上的策略。認識文藝的人,對于人生世相往往見出許多可驚可疑可痛哭流涕的地方,這種較異樣的認識往往不容許他抱駝鳥埋頭不看獵犬式的樂觀。這種認識固然不必定是十分徹底的,再進一步的認識也許使我們在沖突中見出調和。不過這種狂風暴雨之后的碧空晴日,大半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收獲,而且古今中外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之中有幾人真正得到這種收獲?苦悶的傳染性極大,而超脫苦悶的徹底解悟之難達到,恐怕更甚于駱駝穿過針孔。我對于西方文學的認識是從浪漫時代起。最初所學得的只是拜倫式的傷感。我現在還記得在一個輪船上讀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,對著清風夕照中的河山悄然遐想,心神游離恍惚,找不到一個安頓處,因而想到自殺也許是惟一的出路;我現在還記得十五年前,——還是二十年前?——第一次讀濟茲的《夜鶯歌》,仿佛自己坐在花陰月下,嗅著薔薇的清芬,聽夜鶯的聲音越過一個山谷又一個山谷,以至于逐漸沉寂下去,猛然間覺得自己被遺棄在荒涼世界中,想悄悄靜靜地死在夜半的薔薇花香里。這種少年的熱情,幻想和癡念已算是煙消云散了,現在回想起來,好像生兒養女的婦人打開塵封的箱篋,檢點處女時代的古老的衣裝,不免自己嘲笑自己,然而在當時它們費了我多少彷徨,多少掙扎!
青年們大概都有一個時期酷愛浪漫文學,都要中幾分傷感主義的毒。我自己所受的毒有時不但使我懷疑浪漫派文學的價值,而且使我想到柏拉圖不許他的理想國里有詩人,也許畢竟是一種極大的智慧,無論對于人生或是對于文藝,不完全的認識常容易養成不健康的心理狀態。我自己對于文藝不完全的認識釀成兩種可悲哀的隔閡。第一種是書本世界和現實的隔閡。像我們這種人,每天之中要費去三分之二的時間抱書本,至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可以應事接物。天天在史詩、悲劇、小說和抒情詩里找情趣,無形中就造成另一世界,把自己禁錮在里面,回頭看自己天天接觸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反而覺得有些異樣。文藝世界中的豪情勝慨和清思敏感在現實世界中哪里找得著?除非是你用點金術把現實世界也化成一個文藝世界?但是得到文藝世界,你就要失掉現實世界。愛好文藝的人們總難免有幾分書呆子的心習,以書呆子的心習去處身涉世,總難免處處覺到格格不入。蝸牛的觸須本來藏在硬殼里,它偶然伸出去探看世界,碰上了硬辣的刺激,仍然縮回到硬殼里去,誰知道它在硬殼里的寂寞?
本文由【m.cixihy.com情感故事】為您整理搜集!
親愛的朋友們:
這個題目是尊先生出給我做的。他說常接到諸位的信,怪我近來少替《中學生》寫文章,現在《中學生》預備出“文藝特輯”,希望我說幾句切實的話。諸位的厚意實在叫我萬分慚愧。我從前常給諸位寫信時,自己還是一個青年,說話很自在,因為我知道諸位把我當作一個伙伴看待。眼睛一轉,我現在已經糊糊涂涂地闖進中年了。因為教書,和青年朋友們接觸的機會還是很多,但是我處處感覺到自己已從青年儕輩中落伍出來了。我雖然很想他們仍然把我看作他們中間一個人,但是彼此中間終于是隔著一層什么似的,至少是青年朋友們對于我存有幾分歧視。這是常使我覺得悲哀的一件事。我歇了許久沒有說話,一是沒有工夫去說,二是沒有興會去說,三是沒有勇氣去說。至于我心里卻似一個多話的老年人困在寂寞里面,常渴望有耐煩的年輕人聽他嘮叨地剖白心事。
我擔任的是文學課程。那經院氣十足的文藝理論不但諸位已聽膩了,連我自己也說膩了。平時習慣的謙恭不容許我說我自己,現在和朋友們通信,我不妨破一回例。我以為切己的話才是切實的話,所以我平時最愛看自傳、書信、日記之類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文字。我假定你也是這樣想,所以在這封信里我只說一點切身的經驗。我所說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感想,請恕我蕪雜沒有系統。
我對于做人和做學問,都走過許多錯路。現在回想,也并不十分追悔。每個人的路都要由他自己摸索出來。錯路的教訓有時比任何教訓都更加深切。我有時幻想,如果上帝允許我把這半生的賬一筆勾銷,再從頭走我所理想的路,那是多么一件快事!但是我也相信,人生來是“事后聰明”的,縱使上帝允許我“從頭再做好漢”,我也還得要走錯路。只要肯摸索,到頭總可以找出一條路來。世間只有生來就不肯摸索的人才會墮落在迷坑里,永遠遇不著救星。
一般人常說,文藝是一種避風息涼的地方。在窮愁寂寞的時候,它可以給我們一點安慰。這話固然有些道理,但亦未必盡然。最感動人的文藝大半是苦悶的呼號。作者不但宣泄自己的苦悶,同時也替我們宣泄了苦悶,我們覺得暢快,正由于此。不過同時,偉大的作家們也傳授我們一點嘗受苦悶的敏感。人生世相,在健康的常人看,本來是不過爾爾,朦朧馬虎地過活,是最上的策略。認識文藝的人,對于人生世相往往見出許多可驚可疑可痛哭流涕的地方,這種較異樣的認識往往不容許他抱駝鳥埋頭不看獵犬式的樂觀。這種認識固然不必定是十分徹底的,再進一步的認識也許使我們在沖突中見出調和。不過這種狂風暴雨之后的碧空晴日,大半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收獲,而且古今中外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之中有幾人真正得到這種收獲?苦悶的傳染性極大,而超脫苦悶的徹底解悟之難達到,恐怕更甚于駱駝穿過針孔。我對于西方文學的認識是從浪漫時代起。最初所學得的只是拜倫式的傷感。我現在還記得在一個輪船上讀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,對著清風夕照中的河山悄然遐想,心神游離恍惚,找不到一個安頓處,因而想到自殺也許是惟一的出路;我現在還記得十五年前,——還是二十年前?——第一次讀濟茲的《夜鶯歌》,仿佛自己坐在花陰月下,嗅著薔薇的清芬,聽夜鶯的聲音越過一個山谷又一個山谷,以至于逐漸沉寂下去,猛然間覺得自己被遺棄在荒涼世界中,想悄悄靜靜地死在夜半的薔薇花香里。這種少年的熱情,幻想和癡念已算是煙消云散了,現在回想起來,好像生兒養女的婦人打開塵封的箱篋,檢點處女時代的古老的衣裝,不免自己嘲笑自己,然而在當時它們費了我多少彷徨,多少掙扎!
青年們大概都有一個時期酷愛浪漫文學,都要中幾分傷感主義的毒。我自己所受的毒有時不但使我懷疑浪漫派文學的價值,而且使我想到柏拉圖不許他的理想國里有詩人,也許畢竟是一種極大的智慧,無論對于人生或是對于文藝,不完全的認識常容易養成不健康的心理狀態。我自己對于文藝不完全的認識釀成兩種可悲哀的隔閡。第一種是書本世界和現實的隔閡。像我們這種人,每天之中要費去三分之二的時間抱書本,至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可以應事接物。天天在史詩、悲劇、小說和抒情詩里找情趣,無形中就造成另一世界,把自己禁錮在里面,回頭看自己天天接觸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反而覺得有些異樣。文藝世界中的豪情勝慨和清思敏感在現實世界中哪里找得著?除非是你用點金術把現實世界也化成一個文藝世界?但是得到文藝世界,你就要失掉現實世界。愛好文藝的人們總難免有幾分書呆子的心習,以書呆子的心習去處身涉世,總難免處處覺到格格不入。蝸牛的觸須本來藏在硬殼里,它偶然伸出去探看世界,碰上了硬辣的刺激,仍然縮回到硬殼里去,誰知道它在硬殼里的寂寞?
本文由【m.cixihy.com情感故事】為您整理搜集!
聯系方式
提示:聯系我時,請說明在杰姆小屋看到的,謝謝!
發布評論: